人文學科,常被嘲笑為“無用之學”。為了反駁這一說法,辯護者不得不拿出長篇大論來證明人文學科的價值和意義,相比之下,若是某門自然科學遭受諷刺,他們只需將新發明的材料擺上臺面,諷刺者立馬就“啞口無言”,再也不說什么了。即便這新材料為人類社會帶來災難,他們也能輕松地以科學與倫理、發明者與使用者之間的不同加以說明。
如果我們往前追溯,或許會發現,在近代科學和技術的崛起過程中就已經孕育著人文學科將必然衰落的知識結構。而在過去十幾年,人文學科也逐步遭遇了全球性危機。

電視劇《圍城》(1990)劇照。
確實,科學和技術創造了看得見的器物奇跡,呈現的是有用的價值,而文化、語言、哲學、社會和歷史等學科則被認為只會在口頭上說,在紙張上寫,似乎并沒有什么硬性知識門檻,也并無多少實際生產意義。在荒誕的激進科學主義看來,文科甚至是一種麻煩,譬如對生命、隱私、尊嚴和意義的強調會阻礙他們創新。
如果進入到人文學科內部,人們還會發現,這些研究者年復一年說著同樣的話題,持不同觀念、不同方法的人還為此爭吵不休,上百年了,連一些最根本的問題都沒有達成一致看法。同時,也有一些基礎議題,如“二戰”為何發生、隱私為何重要,其結論是顯而易見的,不必多說的,卻有研究者持續不斷地涌入。這兩種景象,都是人文學科批評者和諷刺者不能理解的,他們反而認為這種知識狀態是人文學科無用的表現。的確,人文學科圍繞同一個老問題,為了彰顯某種新意,可能會庸俗地創造新概念、新術語,有的甚至變為所謂學科“黑話”,借助了華麗的詞藻。
英國思想史學者斯蒂芬·科利尼(Stefan Collini)也加入了辯護陣營。同其他辯護者不同,他的論證關鍵是進入人文學科內部,為它的“重復”“爭吵”“感性”尋找意義,唯有接受了這幾種特征,才算得上接納了人文學科。
以下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大學,有什么用?》一書,摘編有刪減,順序有調整。標題為摘編者所起。注釋見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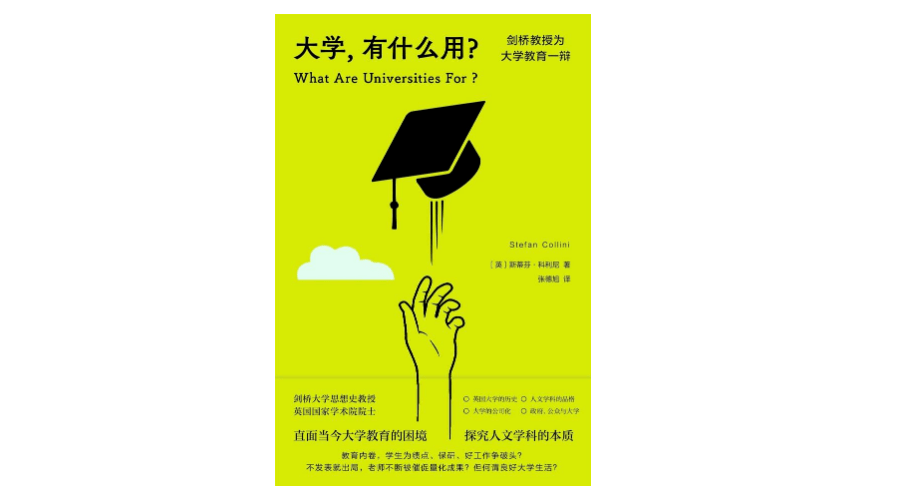
《大學,有什么用?》, [英] 斯蒂芬·科利尼 著,張德旭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守望者,2023年6月。
重新定義“人文學科”
根據最新版的《牛津英語詞典》,“人文學科”有如下定義:“與人類文化有關的學科門類,包含歷史學、文學、古代語言和現代語言、法律、哲學、藝術和音樂等學術科目。”如此定義,恰如其分地凸顯了這一術語的學術地位,它所列舉的學科也不會引起太多質疑,不過可能需要說明的是,藝術和音樂通常只有被當作學術研究對象(例如,藝術史或音樂學)而不是創意實踐時,才屬于人文學科。
在詞典編纂學的角度之外,“人文學科”這個標簽現在也囊括一系列其他學科,這些學科試圖跨越時間和文化的障礙,理解作為意義承載者的人類之行動和創造,重點關注的是與個人或文化獨特性有關的問題,而不太關注那些易受統計學或生物學所影響的問題。
相比人文(研究人類世界)與科學(研究物理世界)之間的迂腐區分,一種更好的表述方式或許是:人口統計學或神經心理學這樣的學科雖然是研究人類的,但只是偶然地把個人或群體當作意義的承載者,所以我們通常不會把它們歸入人文學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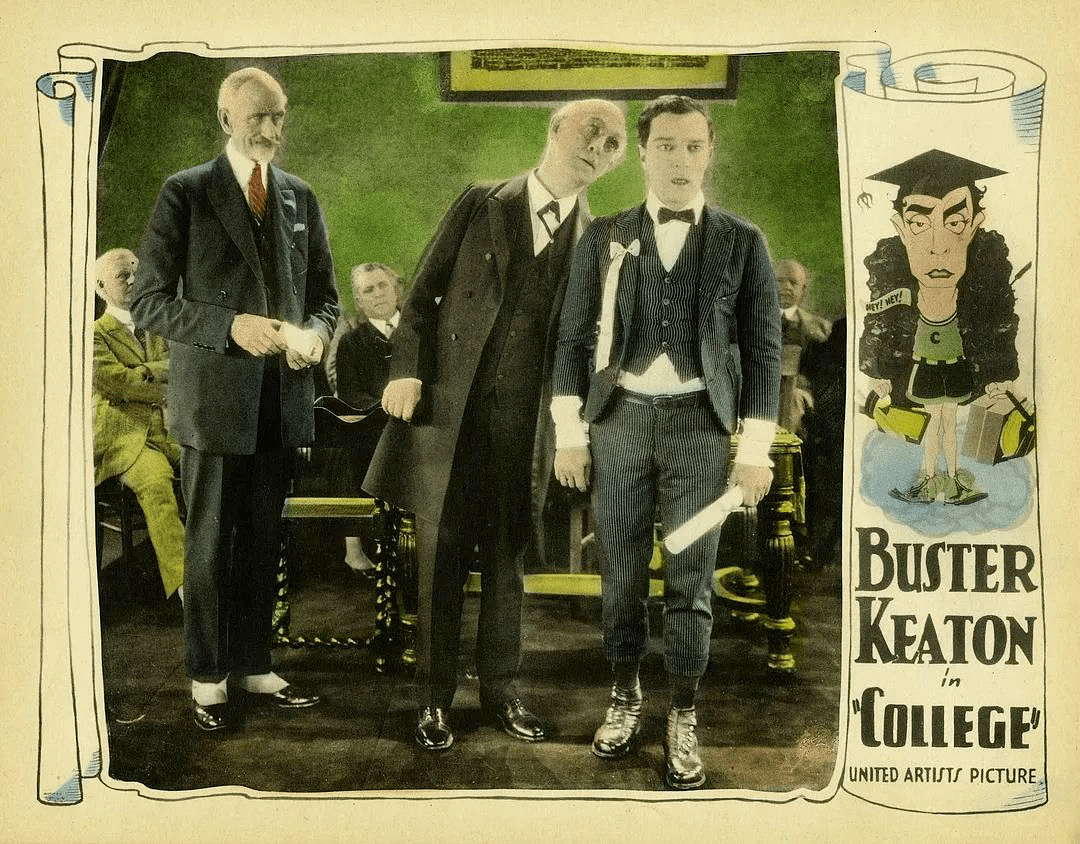
《大學》(College,1927)劇照。
這樣的定性方式,不允許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做出硬性的區分:通常被歸入后者的一些學科,不僅表現出鮮明的理論特征或量化特征,還顯露出人文學科所特有的闡釋維度或文化面向——政治學、人類學、考古學都屬于此類社科學科,盡管它們有著各不相同的人文屬性。有時,同一主題可能同時屬于(被假想的界限劃分出來的)兩個相鄰學科:譬如,政治思想不僅由政治學家來研究,也由思想史學家來研究;過去的社會行為不僅對社會歷史學家有用,對社會學家也同樣有用。對于思維縝密的分類者來說,語言學是一個特殊學科,它既與語言史家乃至文學評論家的研究興趣有一些共通之處,也與實驗心理學和聲學在方法論上存在共同點。
面對“人文學科”邊界的多孔性和不穩定性,有人設法將這個詞限制在某種不容置疑的中心地帶,將這個標簽局限于對西方思想精華和文學經典的研究。這種反應在美國近來針對人文學科所扮演的角色的討論中,尤為清晰可見。在美國,人文學科的焦點一直是教育教學法,傾向于為研讀文史哲經典文本的“偉大之書”課程(“great books”courses)辯護。
但是,以這種方式限制“人文學科”的意涵,不僅完全違背了業已確立的慣用法,而且一些現實理由也導致這種做法不可取。這個標簽須涵蓋完整的古今學問和學術積淀,比如古代語言和現代語言研究,以及歷史、藝術、音樂、宗教和文化等領域的包羅萬象的研究,而絕不僅限于研究偉大作家和哲學家的作品。
人文學科是“自我重復”嗎?
這看似只是一個分類學的問題——對于那些因從屬于某一范疇(而非另一范疇)會帶來利害得失的人而言,分類問題很重要,但從大處著眼,這樣的分類問題難免顯得枯燥無味、毫無生氣。盡管如此,最好在一開始就提醒讀者,統攝在“人文學科”這一標簽下的作品類型是豐富多樣的。

《安妮·霍爾》(Annie Hall,1977)劇照。
人們就此范疇而做的一般性陳述,往往產生扁平化的效果,將人文學科的知識探索描繪為整齊劃一的活動,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我們只需去藏書豐富的學術圖書館逛一圈。速覽圖書館的人文學科書庫,我們會發現,這些不同領域的學術研究如此千差萬別,光看書的外觀就能感受到這一點。哲學期刊上的短論文,有數字編號的命題或布滿符號的句子;一部500頁的歷史著作中,對經驗證據所做的密密匝匝的翔實腳注隨處可見;文學評論集收錄了風格獨特的各式文章。總而言之,人文學科的作品,種類繁多,形式多樣,幾乎與其題材一樣,隨著文化的變遷和時間的流逝而呈現出不同樣貌。
面對一書架又一書架的書籍和文章,外行讀者很容易嘀咕,這些書和文章的內容都是對有限話題的不斷重復,好像再沒有什么新東西可說。當然,到目前為止,學者們對莎士比亞、法國大革命的起因、支持自由意志的論據都已了然于心,應知盡知。當然,在某些情況下,真正的新證據可能會被發現,比如一位幸運的學者偶然發現一件因為被錯誤分類而迄今無人知曉的作品,或者在某位名人后代的滿是灰塵的閣樓里找到了一只手提箱,里面裝著揭示真相的信件。但大多數情況下,外行讀者若有所思地說,當代的人文學者似乎與他們一代又一代同行前輩多年來所做的是一樣的事情,書寫同樣的文本,使用同樣的材料,處理同樣的問題。那么,他們到底在做什么呢?
對智識的永不滿足
他們——我們——大部分時間所做的是憂心忡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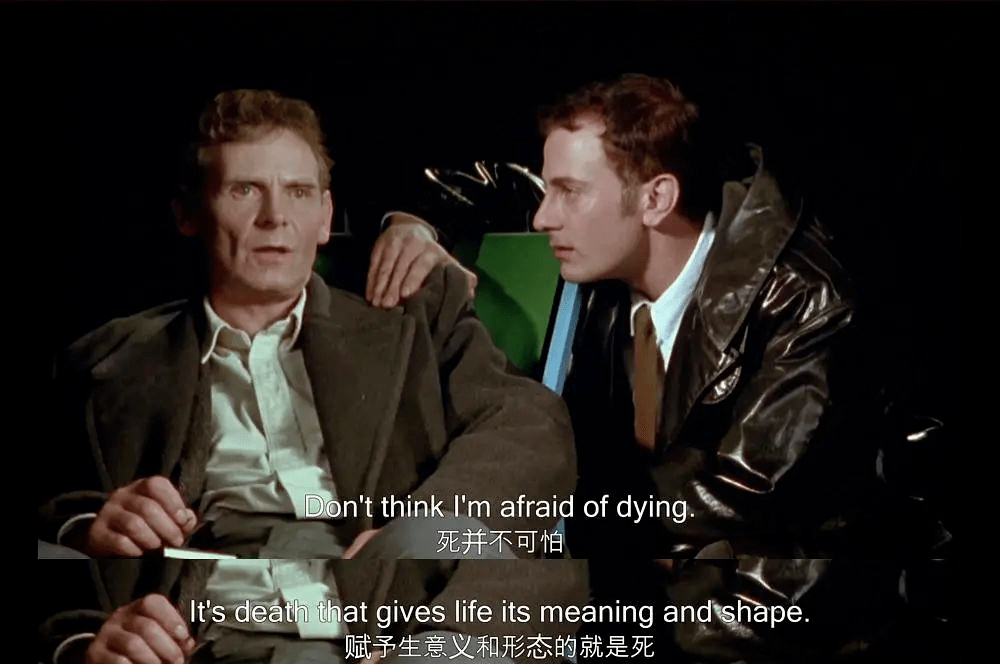
《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93)劇照。
人文學者的常態是對智識的永不滿足。無論發現了多么令人振奮的新證據,或做出了多么富于啟迪的恰當描述,人文學者永遠不能(也許也不應該)完全消除這樣一種感覺:他目前所做出的成果只能算一份臨時報告,總是容易遭受挑戰、被人糾正,乃至無人問津。他會在腦海里尋找一種模式,尋求一種秩序,但這是一個躁動不安、永無休止的過程。
對于人文學科而言,最可能產生影響力的作品通常是書籍,因為它相當于一塊尺寸極為寬廣的畫布,可以通過令人信服的細節,來充分展示其所繪制的圖案。要想使一本人文學科的著作產生影響力,作者必須提出典范性的模式,使之成為該領域諸多后續研究的框架。
就此而言,在剛過去的一代或更久以前出版的書籍中,能夠塑造整個子領域的范例包括:E. P.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或弗蘭克·克莫德的《結尾的意義》(The Sense of an Ending,1967),或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1971)。在某些方面,這些作品從未失去切合現實的相關性。不過,它們幾乎一直受到批評和修正(有時系作者本人所為)。而且,人們感覺,這些著作所歸屬的學術共同體仍在向前推進——或轉移到其他話題,或采用不同的方法,或提出新的問題。
學術共同體能做到這一點,并不完全是發現新的經驗證據的緣故,也不完全是學術風尚的運作,亦非來自外部世界不斷變化的壓力使然,盡管這些因素都可能起到一定作用。更根本的原因是,任何知識的起點都需要被重新思考,任何假設(關于社會如何變化、人們如何行動、意義如何表達)都需要被質疑,任何詞匯都不具有排他性的壟斷地位。這里,學者對知識不滿的生存狀態,演變為一種方法上的準則。在實踐中,它需要經驗豐富的判斷,以決定何時提出不同類型的問題能有效推動知識的進步,何時只會起到無關緊要乃至阻礙性的作用。
但原則上,任何問題都不能被事先否決。別人總是可以重新出發,另起爐灶,找到新的切入角度,從他處入手——那么我們也可以。學者所做的工作永遠是暫時性的、過渡性的。
“知識”,不等同于理解
此處,厘清知識(knowledge)與理解(understanding)之間的分野變得至關重要。
我們對某一特定話題的理解,除了其他因素,還取決于我們對其他話題已有的理解。這個觀點類似于很久以前在所謂的“早期音樂”運動中出現的一個關于尋找本真性的觀點:我們盡可以用那個時代的樂器演奏作品,但我們不能用那個時代的耳朵聆聽演奏。同樣,我們如今無法按照A. C.布拉德利在其經典著作《莎士比亞悲劇》中提出的理解方式去理解莎士比亞,不僅是因為我們對那位作家的理解水平已經有所提高,還因為我們對其他很多東西的理解也發生了變化。
的確,我們現在比一百年前的人知道得更多,譬如我們熟稔莎士比亞文本的傳播或伊麗莎白時代舞臺藝術的狀況。但更為根本的是,我們已經對各式各樣的問題形成了千差萬別的觀念,譬如族裔刻板印象的運作,或婦女的社會從屬地位,以及對戲劇人物的解讀,乃至寫作和意義之間的關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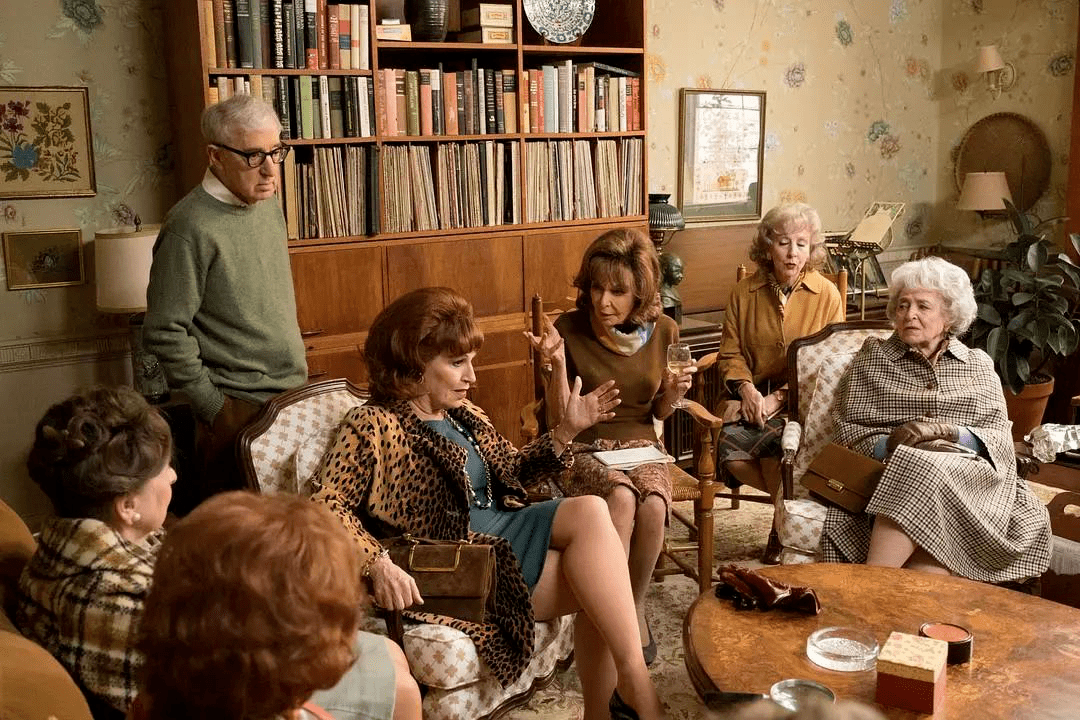
《六場危事》(Crisis in Six Scenes,2016)劇照。
在某些方面,我們的學術研究力圖接近作品被書寫的那個年代的鑒賞力,盡可能熟悉那個年代的語言和種種假設。但是,畢竟是生活在當代的我們在進行理解活動,然后試圖用當代的表述風格把這種理解傳達給當代讀者。我們不能單純地重復人們在一百多年前形成的理解和判斷,即使我們想這么做,也終究力所不逮。
從別的視角入手,可以帶來豐富的新見解和新闡釋。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一個例證是性別(gender)和性欲(sexuality)視角。過去的三十年間,學界對性別和性欲問題的關注,已對眾多學術領域產生了天翻地覆的影響。一個極為顯著的影響是,這一視角使一大批之前備受忽視或不為人知的資料成為人們的關注焦點。
例如,現如今,每位文學研究者對過去幾個世紀里女性作家書寫的重要作品的了解和認知程度,是前幾代學人所無法想象的;同樣,幾百年前,有一半的人口在公共記錄上幾乎沒留下任何痕跡,針對這些人口在公共記錄之外的活動證據,歷史學家開始了系統性的探究和質詢,于是才出現了完整的社會史和文化史領域,而在這之前,這些領域幾乎是不存在的。
與此同時,這種視角的轉變也可能以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方式,激發人們從事新的工作、書寫新的作品。例如,有些道德哲學家和政治哲學家開始向自己發問:評價主體性的時候,評價者所采取的立場隱含了怎樣的男性特征?或者衡量幸福感的某些標準,具有怎樣的性別屬性?誠然,這一連串質問所激發的新主張和新闡釋,未必都能經受隨后的檢驗,但不可否認,整個人文學科的學術格局已然發生了無可爭議的改觀,這些變化在未來也不大可能消失。
永無止境的“分歧”
不過,即使這些變化得到認可,即使所有新話題和新視角都被認為是學術范圍和闡釋能力的合理延伸,外界的觀察者仍然傾向于認為,人文學者似乎并未把大量精力用于新材料的發現上,而是用于對其他學者的反駁上;這不僅僅是在糾正某些事實錯誤或闡釋謬誤,而是否定了其他學者的整個思路。
觀察者問道,人文學科已經以某種形式存在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何還沒能解決思路和方法這些最基本的學科問題?實際上,針對這一曠日持久的爭論,這個觀察結論言過其實。就連同一學科內的敵對“學派”成員之間,他們在合法程序和既定真理方面也有著極為廣泛的共識,這種共識通常并未言明,但遠比他們之間因為分歧而引發的吸人眼球的對峙多得多。

《新生》(The Freshman,1925)劇照。
話雖如此,人文學科內部確實存在諸多根本性的爭議(不是說理科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內部就不存在這樣的根本性爭議)。面對這一事實,正確的回應也許不是將人文學科視為失敗的學科,而是要認識到,該領域的工作與人類最基本的生存狀況是何等息息相關。毫不驚訝,沒有人能就“何為生活”問題達成一致,甚至連如何表述這個問題,使之成為學術探究的課題,也無法達成一致。因此,不足為奇,所有試圖理解古今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努力,無論其在概念分析和證據處理方面如何訓練有素,都會復現這種根本性的分歧。
這就自然引出了“理論”問題。
在文學和歷史學科,“理論”是當共同的討論起點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時候所出現的東西。這種說法有助于我們理解“理論”所起的作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英語世界的文學評論家在諸多問題上存在分歧,譬如某些雅各賓派戲劇的作者身份問題,或者濟慈對丁尼生的影響,或者D. H. 勞倫斯到底是不是一位偉大的作家,但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對評估文學價值的合法性乃至可能性,或者對“文學”這一范疇是否存在等問題并無分歧。然而,當所有這些基本概念和評估程序被陌生化,故而彰顯出其文化偶然性而非邏輯必然性的時候,討論的起點就會發生變化,于是討論就必須轉向更為理論化、更為抽象化的層面。

紀錄片《揭秘莎士比亞》(Shakespeare Uncovered,2012)第一季畫面。
再強調一次,這種理論化或抽象化不是一種病態,也不是由于學科中人對公認的經典名著無話可說,更不是由于文學學者對文學失去興趣(盡管有些人可能確實如此)。確切地說,它可能是一個健康指標,最起碼是一個跡象或征兆,表明學者們不能也不應該免疫于知識更迭。在一個極為多元化的社會,知識更迭和思想變遷是自然而然發生的,某些傳統精英們所共享的那套假設和舊觀念已經無法獲得普遍認同。
“科學”抵達不了的地方
目前,人文學科也常被稱作“人文科學”(the human sciences),它的自我描述是:該學科內部的各個科目所共享的獨特活動是“批判”。這個備受青睞的自我描述,反映了人文學科的一貫主張。批判總是旨在挑戰任何起點、假設或參考范圍的被給予性。通過挑戰這樣的起點,它通常揭示潛在的險惡利害關系。不消說,就實現某些意圖而言,批判可以是一種完全有效且確實必要的戰略追求。但在具體的實踐層面,出色的科研工作,類似于酣暢的交談或任何有價值的人際關系,取決于構想一個更為開闊的共同世界的能力。
這樣的世界未必是邪惡的或排外的,也未必可以與某一社會群體或利益相提并論。從諸多異己的背景出發,人們可以了解形形色色的新世界。由此一來,個體之間將會產生越來越多的共同點,這遠非固守先前的“方法論立場”或“社會身份”所能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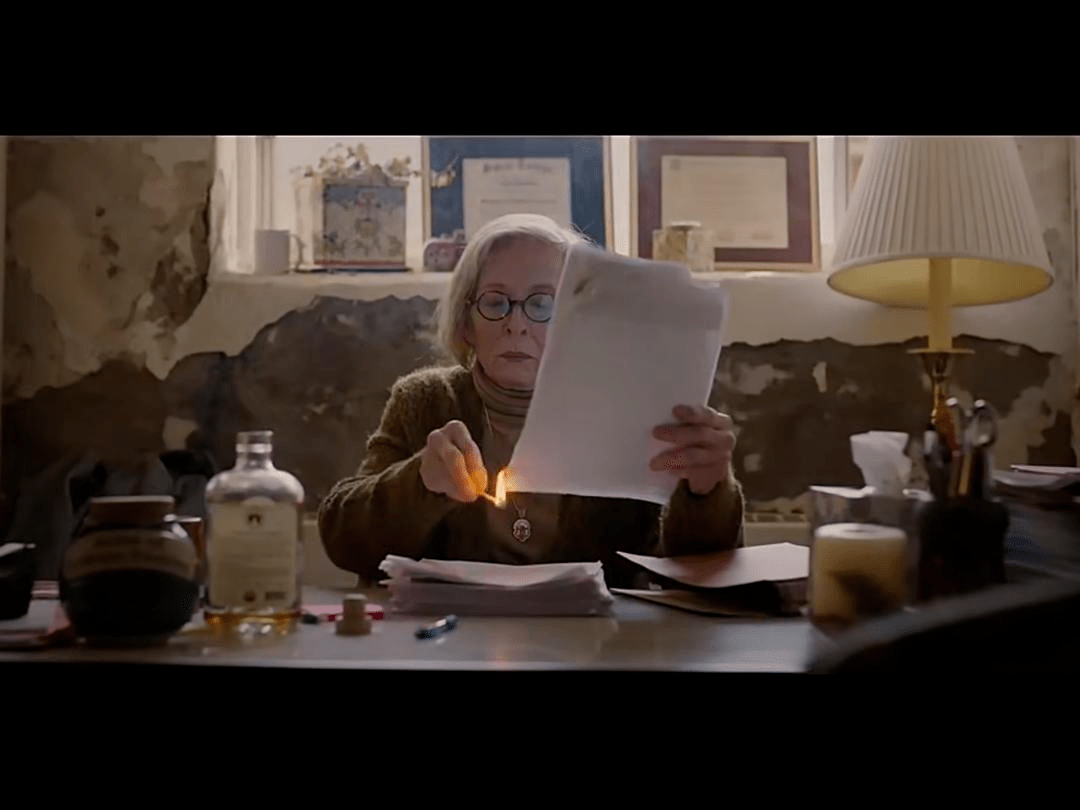
《英文系主任》(The Chair,2021)劇照。
在此基礎上,個體之間就一本書或一件事展開的思想交流,會更富有成效。批判模式堅信,任何論點都具有社會的在地性(locatedness),并力圖解構之,從而打造自己的叛逆形象。然而,這樣做的后果是不斷地將討論轉移到一個先驗的立場上,從這個立場出發,找到任何特定交流中都存在的限度。這在哲學探究中自有其意義,但過于迅速地轉向元理論的立場,往往會阻礙或挫敗我們對具體文本的探討,使我們無法領略文本獨具的神韻,因此批判模式不能成為人文學科所有工作的統一處方。
這種情形可以用一個比喻來解釋。這就好比一群操著不同“語言”的個體,理想情況當然是讓他們能就某一問題進行最豐富、最細膩的交流,這要求他們必須去學語言、做翻譯,而不是為了迎合大眾而刻意簡化,將之化約為相當于世界語的通用知識。
此外,只要“批判”涉及具體實例,它所具有的“懷疑闡釋學”傾向,既可能產生賦能作用,也可能產生限制作用。以批判為原始動力的學術作品,存在一種奇怪的不對稱性:它對作為研究對象的人物有著極為苛刻的設想,對研究者本人的預設立場反而放松警惕。我的方法恰恰相反:對于我們所研究的人類行動主體,要盡量保持一種想象的同情;與此同時,對于我們自己的闡釋機制,要盡量持有一種懷疑的批判。深度理解的達成,不僅僅需要我們敏于解構,更需要我們心懷慈悲,盡可能給予熱情而充分的回應。
認同、同情、想象等過程可能暗示一種散漫無序的主觀主義,因此近幾十年來,人文學科一直試圖用更為嚴謹的時髦方法論取締它們。但實際上,無論是在學術工作中,還是人類經驗的其他方面,它們對人類實現全面透徹的理解都是必不可少的。
原文作者/[英] 斯蒂芬·科利尼
摘編/羅東
編輯/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