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三聯美食

『放一點韭菜胡蘿卜炒的臊子,加鹽巴、醬油、醋,再來上一大勺油汪汪的油潑辣子,坐在堂屋中,吹著過堂風,呼呼嚕嚕就是一大碗。』
作者 / 扶桑
在關中平原上,面食被心靈手巧的主婦們玩出了無數花樣。單論面的做法,有韭葉面、棍棍面、褲帶面、蝴蝶面、驢蹄子面……單論面的吃法,有燴面、湯面、炒面、拌面、油潑面、蘸水面、漿水面……若是將面的做法和吃法排列組合,便是一年365天都吃面,主婦們也能保證天天不重樣。
在這片平原上生活了20多年,我也長成了天生的面食胃。即使現在早已定居南方,周末也必得親手和面搟片,做一碗地道的關中面。而我最愛的,還是可湯可干可炒可拌的關中麻食。
麻食,并非關中所獨有,甘肅寧夏一帶亦食用。關于麻食的吃法,傳說大約有2400多年的歷史,已知最早的記載大約在元代。當時的飲膳太醫忽思慧所著《飲膳正要》中載:“禿禿麻食,一作手撇面。以面作之。羊肉炒后,用好肉湯下,炒蔥,調和勻,下蒜醋香菜末。”明朝人所輯著的《居家必用事類大全》里也說:“禿禿麻食,又名禿禿么思,如回族食品,用水和面,劑冷水浸,手搓成薄片,下鍋煮熟,撈出過汁,煎炒、酸水,任意食之。”可見,在元明之際,麻食已經相當流行。
圖 / 視覺中國

比起一般的面條來,麻食其實是個相當考驗耐性的食物。須得先和面,揉面至面團軟硬適中,柔中有筋。然后搟成厚片,切條。再搓成食指粗細,撒干面粉。七八根面條兒整理好,切小丁,拇指蓋大小。然后,在院子里瘋玩的小孩子們便會被喊到廚房來,洗了手,在長長的案板前站成一排,完成最后的工序——做麻食。
我的家鄉做麻食一般有兩種手法。一種是搓麻食,即大拇指摁在面丁上,使勁往前一搓,筒狀的一個小麻食就搓好了。還有一種是捻麻食。拇指仍是摁在面丁上,輕輕往下捻著按,成型的麻食中間薄四邊略厚,因此又被稱為“捻捻”。
麻食四季可食,但以夏季吃得最多。何也?春忙耕種秋忙收,冬季的小炭爐子小案板又難以施展,自然就夏天吃得多。
若說常規的面條是關中人的日常,麻食就更像是農閑時的花樣。炎炎夏日,關中的氣溫常常能達到三十七八度。蟬在老槐樹上不停歇地鳴叫,風扇呼呼吹個不停,人躺在鋪了滿地的涼席上,仍覺得渾身黏膩,稍一動便是一身汗。這時最渴望的,是這世間所有的涼。雪糕,冰鎮西瓜,井水中冰過的糖漬西紅柿;涼粉,過水面,涼拌面,漿水魚魚,樣樣吃了個遍。終于沒啥吃的了,我媽大手一揮:今個兒吃涼拌麻食。
我爸殷勤地把風扇端到廚房插好,然后生火燒水。我弟就去院子里端干柴,割一把韭菜。我和我媽一人一側,雙手開弓,站在案板前搓麻食。搓好的麻食下了鍋,點一回水,便可撈至裝了涼開水的不銹鋼盆中。
吃的時候,用笊籬瀝去水,盛入碗中。放一點韭菜胡蘿卜炒的臊子,加鹽巴、醬油、醋,再來上一大勺油汪汪的油潑辣子,坐在堂屋中,吹著過堂風,呼呼嚕嚕就是一大碗。

關中夏天多連陰雨。一下雨,農家人就閑下來了。年齡大的,往往會窩在炕上美美睡上一晌午,才好解一解田間勞作的乏。年輕人,往往三個五個湊做一堆,東家長西家短地說說閑話,一會兒捂著嘴小聲唏噓一會兒又拍著大腿笑得前仰后合。小孩子呢,更是精力充沛。打彈珠,拍畫片,跳房子,農家磚鋪的寬敞空地上,撒了歡地玩,盡了情地喊。
不知里屋誰問了一句“幾點了”,正聊得起勁的主婦們抬頭一看墻上的掛鐘,“哎呦”一聲,該做午飯了。這家的女主人便拿把小刀,披一塊塑料布,踩著瓦片走到菜園子里。這個大嬸說“給我割把韭菜”,那個小媳婦羞答答地讓“摘幾個豆角”,還有那嗓門大的婆婆喊著“別忘了拔幾棵小白菜,我家掌柜的愛吃”。
末了,這家的木耳干香菇,那家的黃花小香菜,都打發了小姑娘小小子送了來,然后一把放在廚房外的笸籮里,邊喊著“我媽讓我拿來的”,邊用手遮了頭噠噠地跑出了門。待女主人抓了兩把新買的零嘴兒趕出去時,早就跑得沒了人影兒。
這么多菜做點啥飯好呢?當然是燴麻食!
先麻利地捻出一桌麻食,什么豆角啦,香菇啦,木耳啦,小蔥啦,全都切成丁,一鍋炒。灶間的火燒得旺旺的,不一會兒鍋就滾了。麻食被噗嚕嚕下進滾水里,案板上的面掃做一處,用手掬了,撒進鍋。點一回水,不大會兒工夫又開了。麻食不斷翻滾著,冒出泡泡,鼓漲得快與鍋沿平齊了。這時,將炒好的菜倒進去,打散的雞蛋沿著鍋邊淋一圈,幾下就成了嫩黃的蛋花。青菜扔幾棵,蓋了鍋蓋,撤了柴火,讓麻食和菜咕嘟得更濃稠一點。
不待催喊,屋子里睡覺的,家門口風跑的,都循了香味兒鉆進小小的廚房。
伴著遠山近煙,伴著陣陣犬吠,以及滴成了線的屋檐水,熱熱乎乎地吃上這一碗雨天的燴麻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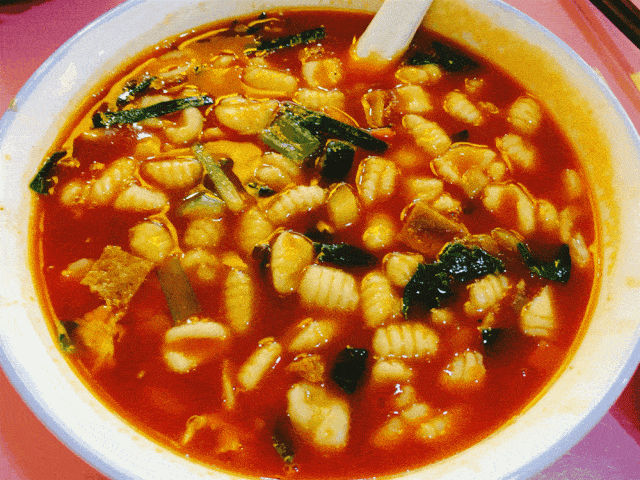
連下了幾天的雨終于停了,但還下不了地。這個時候,我媽就會和我姨約好了,拖家帶口去二里外的鄰村看望外婆。回娘家攜禮是外嫁女的孝心體現,但農家人最是講究個經濟實惠。看望外婆帶的往往就是奶粉、雞蛋糕、香蕉一類好消化的食品。去我外婆家要翻越一座小小的荒埝,忙天少有人走,一下雨,路邊就會長出一朵朵小小的地軟。我們會提前準備袋子,然后鉆進埝邊的枯草間,一陣地毯式搜索,便摘了滿滿一袋子地軟。
到了我外婆家,八九口人把個小小的房間擠得滿滿當當。我外婆弓著背,一步一踱,從電視下面的柜子里取出不知珍藏了多久的零食,給我們吃。
茶水喝了兩泡,家里的瑣事地里的莊稼也說得差不多了,我外婆、姨媽還有我媽就進了廚房。有什么菜就用什么菜,通通拿來燴麻食。新鮮的地軟扔進鍋里,同著麻食菜丁親親密密地翻滾,煮得軟韌的粉條也猶如亂云飛渡,帶出些山野的氣息。點上幾滴香油,灶臺上已齊刷刷擺出了八九個碗。外婆一聲令下,我們幾個小的端了熱氣騰騰的麻食就坐在門外的石墩子上,你撞下我的肩,我拍拍你的背,然后笑嘻嘻地吃完一碗麻食,一溜煙又跑去了灶間。
午飯后往往會再閑談上一會兒,才順著原路往家走。外婆就一腳跨在門檻上,遠遠地叮囑我們好好看路,不要打鬧。我們一邊應著,一邊喊:“外婆,過幾天麥收了我們還來,到時蒸地軟包子……”
童年的情形一晃而逝,卻常常出現在夢中。想家的時候,我就煮上碗熱乎乎的燴麻食,吃著吃著,仿佛又回到那永遠難忘的小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