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權轉載自“南風窗”( ID:SouthReviews)
原標題|男孩被逼吃屎,我們都誤解了孩童之惡
作者: 永舟
若非以視頻形式傳播開來,真的不敢相信,這竟然不是假新聞——“一小孩被逼吃糞便”。
7月1日,山西晉中介休市委網信辦發布通報稱,此事系3名未成年人欺凌1名未成年人。對此,公安機關已經立案,對實施欺凌者及其家長進行了嚴厲批評教育,責令家長對子女嚴加管教,并對被欺凌者及家長賠禮道歉。目前,雙方家長已經達成和解。
不論代入哪一方角色,這都是一件讓人感到不可理喻、匪夷所思、火冒三丈的事。其侮辱性與惡心程度,甚至超出了一般校園霸凌的常見范疇。
很難想象,這個年齡的孩子,同理心與共情能力竟匱乏到這個地步。
短視頻時代,我們見到了太多超出日常經驗和想象的、無關“天真爛漫”的孩童。
在今年3月曝出的另一支視頻里,一7歲女孩將一個陌生的4歲男孩抱起來,毫不猶豫地扔進了井里。更甚的是,當男孩出于求生欲本能將雙手支撐在井邊時,女孩甚至還前去將他的雙手掰開,讓后者徹底跌入井內。
2022年6月,湖南一名8歲男孩毆打一名2歲男孩,并將后者從17樓推下,事后,8歲男孩竟然布置假現場,偽裝成意外墜樓,差點騙過所有人。
更早一點,2019年10月,大連10歲女孩遇害,尸體在距家僅100多米的灌木叢中被發現。經警方調查,兇手為一個13歲的男孩。

《無人知曉》劇照
不論是各式校園霸凌與青少年犯罪,長對幼、或對弱小動物的欺凌,發生在孩子們身上的惡,常常存在較為清晰的位次和絕對力量對比,就像原始叢林社會那樣簡單、粗暴和野蠻,很多時候并不能找到一個明確的功利性動機。
與此同時,人道主義者很容易因為對人類抽象的想象和博愛,忽略了個人具體的性質與責任。
近年來對刑事責任最低年齡的爭議愈烈,人們對于孩童的惡,還是太缺乏解讀能力與想象力。
一種常見的思維惰性及慣性,是籠統歸咎于家庭教育的失范,父母監管的失職。或者,滑向經驗主義之上的,某種文化觀念里常見的囫圇邏輯:TA還是個孩子!
——是的,還是個孩子。因此,更不能僅以譴責父母或以“保護未成年”的概念了事。
余華寫過一篇中篇小說《現實一種》,住在一起的兄弟倆分別有兩個兒子,小的那個尚在襁褓,大的那個4歲。一個寂靜明媚的午后,4歲的堂兄把堂弟從搖籃里抱起來,走到陽光底下,然后在沒有任何征兆和緣由的情況下,高舉雙手,把弟弟狠狠摔死在了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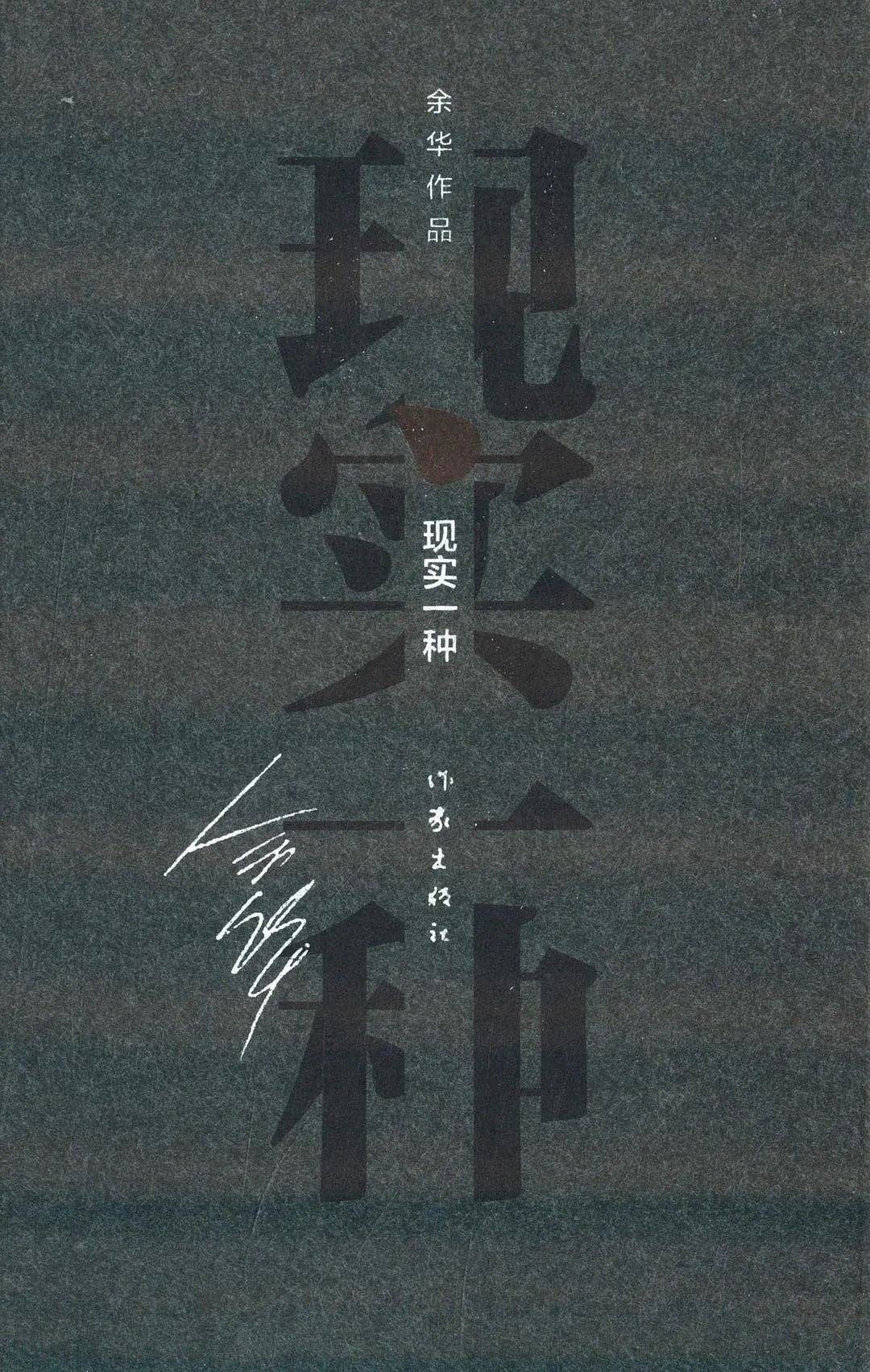
《現實一種》
看見從弟弟身上流出來的血,哥哥不僅沒有恐懼,反而產生一種異樣的好奇。他伸出自己的舌頭,舔舐了嬰兒的血液,并且感到一股奇妙的滿足。
這看似毛骨悚然的描述,被余華解構為一種欲望的本能、暴力的本能。無關理性和利弊權衡,僅僅出于一種天然的,動物面對鮮血的渴望。
故事后面,4歲的男孩被自己的叔叔,也就是堂弟的父親踢死了。雖然符合人類社會“冤冤相報”的基本法則,但這背后折射出來的,反而是一種非理性的、野蠻的血親相殘,是站在人性反面的殘酷寓言。
其實余華最擅長書寫的主題,不是現實主義的苦難,反而是這種具有點先鋒色彩的,直接叩啟人性深處的暴力與野蠻。《活著》之外,他的很多作品都能幫我們以一種更克制、冷靜的視角,去審視人性天然攜帶的一些情感和欲念。
比如在講述自己親身經歷的短篇《闌尾》里,余華以一種近乎于幽默的輕松語調,講述了童年時期自己與哥哥單純因為好奇,在父親闌尾炎發作時,拒絕帶他去醫院,而是割掉了父親的闌尾。
父親的身體受到了嚴重的損傷,再也不能當醫生了。但兩個孩子卻能以一雙無辜單純的大眼睛,將一切罪惡消匿在淚汪汪的童涕之中。
兒童并未意識到自己的過錯與罪惡,他們所做的一切,不過出于無知與懵懂,出于一種單純的、非理性與功利性的好奇心,甚至是一種“天真”。
幾十年后,另一個“80后”作家鄭執在小說《生吞》里寫了這么一句話:“成年人的善是復雜的善,孩子的惡才是純粹的惡”。
“天真”,這個看似美好的形容詞,意味著純粹的、去功利性的無知。只不過,長久以來,我們都習慣將這種無知下意識地預設為善意。

《小偷家族》劇照
因此,對于孩子們犯下的過錯甚至是罪惡,成年人的批評大多指向“行為”而非“內心”。是“做錯了事”的結果論,遑論什么惡意與惡念,在這方面堅持“論跡不論心”。
用孟子的性善論更好理解:惡是后天習得的,而善是與生俱來的。
在還不懂得一項舉動能給自己帶來的好處和利益時,一個孩子選擇做出善舉,容易被視為無心的自然流露。
不過,照此理推,惡行,在孩子們心中也應不受功利主義制約,因無知而無懼。
美國認知心理學家保羅布魯姆在著作《善惡之源》里,通過實驗和數據闡述了這樣一個結論:即使是不會說話的嬰兒,也具有最基本的正義感,他們會產生同情,甚至會判斷人的好壞。
但相應的,這些孩子身上也具有欺騙、蠻橫、虛偽、懶惰、冷漠、自私等惡劣天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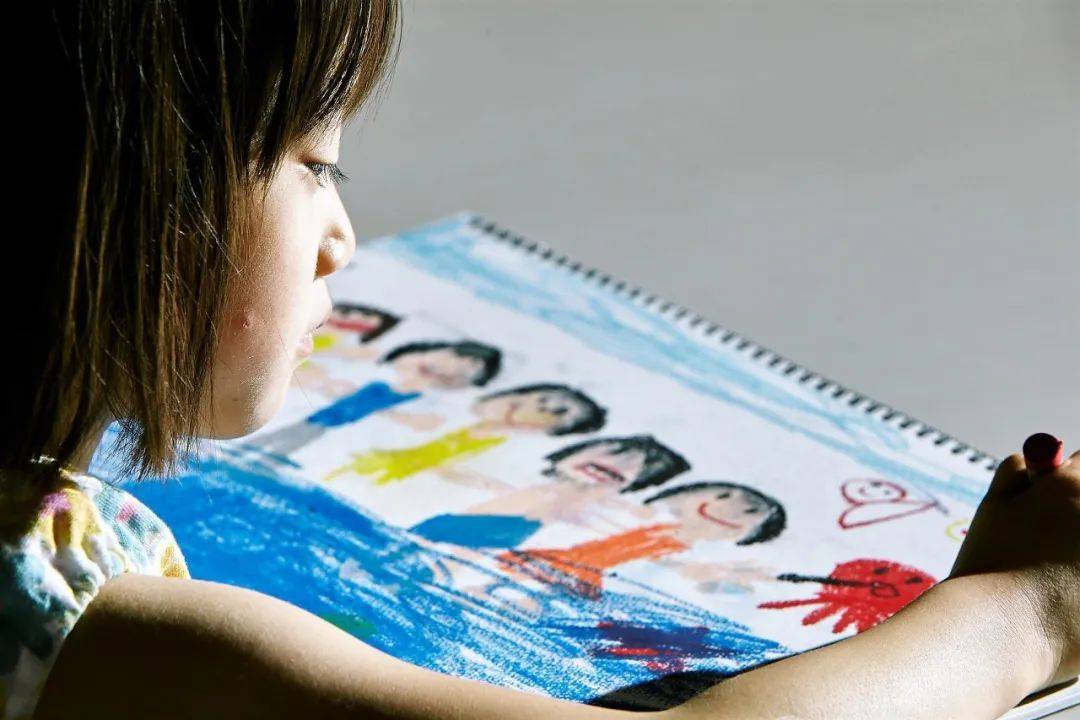
《小偷家族》劇照
只不過,與成年人不同,因為社會化尚未發展完全,孩子們并不會受到良心的譴責,也難以受到道德、法律的制約。因此,惡的產生反而更自然而然,坦蕩輕松。
反觀荀子的性惡論就很有意思,“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這并不是說“性本惡”,并不是說一個人生下來就是惡的,而恰恰是指并不存在“本始材樸”自然之性。
人類的天性里本就包含善的成分,但同時也包含惡的部分。好奇心、單純與直白,是兒童特有的天性,但暴力、血腥、殘忍,同樣是生命的其中一種本能狀態。
但荀子認為,如果順應自然本性,就往往會引起惡果。
有人又要說了,孩子是教育的產物,在進入社會之前,家庭養育者應當為他們的一切行為負責。
這是目前占據社會主流的教育論,即將孩童的一切行為歸咎于父母教育的影響。不論是犯錯還是做好事,似乎孩子都是父母行為與觀念的延伸,是教育體系內的“產物”。

《小歡喜》劇照
還是以小說《現實一種》為例,故事里,家庭環境的確是個不可回避的因素。兩個孩子的父母關系并不和諧,父親常常對母親家暴。另外,家中還有一個孤獨的老母親,說話不被重視,心情無人照看,甚至連病痛都只能自己呻吟。
常言道“言傳”與“身教”,成年人通過自身行為搭建的無意識環境,對孩童而言同樣具有耳濡目染的教育作用。
不過,“教育”一詞(ēducātiō)最早從希臘文誕生時,主要指引領個體“生命性”的轉向,誘出萬物之“本相”,側重于一種寬泛的浸潤、誘發與啟迪。
放在現代社會,環境是每個人面對的最重要教育者。父母在法律上作為孩子的監護人,但學校、同輩、社會制度等多方面要素,也綜合構成了對一個孩子的教育容器。
有時我們看一些校園霸凌的視頻,帶頭打人的那個孩子,或許反而氣勢沒那么足,甚至偶爾退縮。而真正的霸凌“頭目”,其實是舉著鏡頭拍攝的那一個。在更高威的壓制下,施暴者已經被鉗制進了一個真空的階層環境,只能硬著頭皮,朝著更弱者一拳一拳揮去。

《悲傷逆流成河》劇照
還有法律,同樣是一項構成社會環境的重要元素。多年來,凡未成年人犯罪的新聞,總會激發出對現存“未成年保護法”體系的譴責。很多人認為,程度遠遠輕于成年人的懲治法,反而助長了未成年人恣意犯罪。
但這種觀點其實更多是站在成年人角度,以成年人的立場和處事方法,對已發生的事情做出的發泄。
實際上,除非將“未成年人保護法”體系自學前教育階段就納入課標,否則,指望孩子們自知利用規則來作惡,其實還是件過于戲劇化的事。
此外,法律無時無刻不在改進與完善中。羅翔在《法治的細節里》說,“法律的正義不可能是完美的正義”,有時追求成年人在功利角度的最優解,反而可能事與愿違。
歸根結底,得把社會當作一個整體環境來看待。別以為孩子們不懂社會學,當他們產生群體意識時,社會性就開始生效了。而群體性,是人類與善、惡同等生長的另一大天性。
認為“惡出于人猶如蜜產于蜂”的英國作家威廉·戈爾丁,在曾獲諾貝爾獎的《蠅王》里,講述了一個被環境激發出本性之惡的故事。
一群12歲以下的男孩流落荒島,起初,為了生存和獲救,大家還能在大男孩的帶領下和睦相處,搭棚、生火,堅守文明秩序。但當玩忽職守、分配不均、規則混亂等問題產生,彼此間的矛盾就開始激化。

《怪物》劇照
漸漸地,大家忘記了求救的初衷,野蠻和專制壓倒了這群孩子原有的童心和人性之善,整個荒島變成野獸島,陷入打獵、廝殺的混沌狀態中。
整個過程,將人的生物性層次的惡,過渡到了社會性層次的惡。孩子們沒有被任何老師和家長教育,他們只是被他們所處的環境所教育。
這部極端的、寓言及實驗式的小說本身存在很多爭議,但在孩童天性這方面,它依然引我們向更深處思考:都說善惡一念之間,這中間微弱而至關重要的“一念之差”,究竟“差”在哪里?
當天性里的惡被牽引出來,甚至成為主導,構成善意的重要元素——同理心與共情能力,就相對應地劇烈萎縮了。
前段時間,虐待動物問題掀起過一輪熱議。而不少犯罪學與心理學專家都曾指出,相當一部分刑事罪犯曾有虐待動物的前科,后者,提前昭示了他們同理心與共情能力的匱乏。
研究那個話題時,我偶然在網上看到一張美國連環殺手Albert DeSalvo的童年照片。照片里的男孩面朝鏡頭微笑,懷里抱著一只貓。心理學家分析認為,他捏住小貓脖子的那只手,昭示了這孩子對生命的痛楚缺乏天然的理解與感知。

《波士頓絞殺手》劇照
逼同伴吃糞便同理。普通人看一眼,甚至是想一想,都會感到反胃至極的行為,在他們那兒卻毫無心理障礙地被合理化了。
對這個世界的感知,對基本善惡美丑的認知,也失調了。
在我念小學一年級時,有幾個孩子喜歡結群找我“玩”。玩耍的內容是假扮醫生與病人的游戲,我總是扮演病人,被他們用牙簽假裝針頭,貨真價實地扎在手上、腿上。
這件事我從未告訴老師或家長,自然不是因為樂在其中,而是有著自以為更重要的考量:如果把不滿挑開,那我便再也沒有朋友了。
此外,作為從來溫順文靜的“乖孩子”,我不愿談及那些關于欺負、暴力與疼痛的話題,我得維持自己云淡風輕的好形象。

《無人知曉》劇照
日本作家、詩人谷川俊太郎為心理學家河合隼雄的著作《孩子的惡》寫了一首詩:“不可以撒謊,我就微笑著沉默/自己真的在想什么,跟誰也不會說/我是個乖孩子,所以,我是個壞孩子。”
什么是“乖孩子”?想必東亞家庭里長大的孩子深有體會。不哭不鬧,懂得察言觀色,最好無師自通地學會成年人制定的所有規則,比如知道物歸原主,懂得尊老愛幼。
但這其實是一種成年人視角的偷懶。河合隼雄認為,孩子太過平靜,就像“整整一年每天都是大晴天,從來不陰天下雨”那樣令人難以想象,反常且可怕。
“圍繞著規則,會出現人與人互相沖突的機會。把規則當作防護的盾牌,自己躲在后邊,是做不成事的。把規則作為一個切入點,人挺立在前邊,才有意義。”
在《孩子的惡》里,河合隼雄將“孩童之惡”放在校園霸凌、偷竊等“違法亂紀”情境里去看待。沒有一種惡行能脫離規則與環境成立,母貓吃掉自己最孱弱的孩子,在動物界合情合理,在人類看來卻無比殘忍。

《告白》劇照
同樣,在大人看來,孩子伸手向不屬于自己的東西,就是沒教養,就是作惡甚至壞種。
這里面不可或缺的一環,是成年人與孩童之間的交流斷層。
規訓和懲戒,是東亞大家長文化里教育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日常語境內,我們常指的教育,往往是約束和規訓行為,是告誡孩子不能怎樣做,應該怎樣做,但鮮少站在他們角度去看待世界,哪怕那個視角荒謬至極。
那太復雜了。一個“未發育完全”的頭腦和世界,在成年人看來混沌而蒼白,去理解他們就像理解一幅未完成的畫,怎么解讀都不對。更多的情況,理解的嘗試,只是為了更好地管教他們。
在那部著名的少年犯罪題材日本電影《告白》里,天才少年渡邊走上殺人藏尸的道路,起因僅僅是想吸引拋棄自己的母親的注意。“要是我也成為罪犯的話,母親會不會趕來呢?”

《告白》劇照
而電影里另一位少年犯直樹下村,則是與渡邊相反的另一種親子錯位的悲劇。當直樹得知自己喝下了帶有HIV病毒的牛奶,極度的悲傷裹挾了他。他堅信,此事敗露后,自己一定會被母親趕出去。
直樹患上了嚴重的心理疾病和潔癖,最終殺死了自己的母親。
另一部中國觀眾更熟悉的少年犯罪題材電影《牯嶺街殺人事件》里,犯罪行為同樣被楊德昌克制冷靜的鏡頭消解了,重構為一種少年世界的崩壞。世界觀的崩塌,信仰的崩塌,有句話評價此片為“弱者捅向弱者的刀”。

《牯嶺街殺人事件》劇照
只不過,在大部分情態下,兒童的“心”被“跡”掩埋,在他們成長為法律與道德各方面意義上完整的“責任人”之前,他們那些詭譎的、因為各種原因扭曲的內心世界,往往被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
一個少年兒童的“崩壞”,或許比成年人想象的容易,正如我們所目睹的暴力與惡意那樣,隨處落地,野蠻生長。要理解“心”與“跡”中任何之一,都不得不將二者結合起來。
文中配圖來源于網絡
關注它,能讓你聽到更多真話,
多一分對世界的理解。
· 一 周 熱 點 回 顧 ·
他們需要社會的更多關注↓↓↓